1986年,黄建新完成了电影《错位》:一个原本为应付无聊工作而被创造出的“机器人”,随着时间推移拥有了自己的个性,甚至插手“主人”的生活试图取而代之……在30多年之前选择用影像探讨尚未被广泛认知的人工智能概念,他的这次创作有着可以被定义为先锋的时代精神。
有趣的是,当时间来到2023年,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某种前瞻性的想象,而是全面进入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。
《错位》也在此时完成了它最恰逢其时的“归位”。与大部分比这部电影更年轻的观众进行交流,让黄建新感觉很奇妙,“我其实挺紧张的,随着年纪增长,人肯定会变得有点迟钝,但我不想停下来,还是想往前走。” 电影自然也不例外。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,“AI”通过各种方式加入到创作与讨论之中:由人工智能绘制的影展海报;开幕式上,费穆、卓别林等“大师”在科技加持下“亲口”向年轻观众阐述创作理念;电影人围绕AI接下来会怎样改变行业提出各自明确的观点……
“Keep Rolling”,不停向前。这也是黄建新这场大师班确定下的核心主题。除了由展映影片《错位》引出过去先锋的创作,如今成功变换更多身份,成为行业“金牌监制”的黄建新也还畅谈了关于当下行业、市场发展模式的理解,以及作为最早一批关注人工智能的创作者,对于AI与电影未来交互的想象。
沿着过去—现在—未来这条“不停向前”时间坐标,我们整理了黄建新关于探索的成功与失败、新主流类型创作,AI将如何改变电影的思考与答案。
(以下内容根据黄建新自述整理)
过去
宁肯在探索中失败,不在经验中苟活
《错位》在疫情的3年里,又一次在网络上被“炒”起来。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问我,你那时候怎么会有一个AI的概念?我说没有,我拍的是荒诞喜剧。之后有人把我送审报告里填的内容翻了出来,说“你自己写了某某某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,替他开会”,其实我都忘了。
在这之前,我本来准备拍一个故事是讲住房问题的。后来我跟很好的编剧朋友一起讨论了一个多星期,又写了两个星期,《错位》就准备开拍了,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偶合成功的电影。
我是个从小脑子里就爱乱想的人,拍《错位》的时候,我自然想做个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工程我不懂,比如像美国科幻片拆开无数的电路等等这些,我们做不了,就想用荒诞性跳过科技逻辑,只写我们实际的灵魂和真实的人,用最真实部分和最虚假的部分对立,表现出人格分裂或者被异化的矛盾中的故事。

当时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口号是“宁肯在探索中失败,不在经验中苟活”,就贴在我们办公室里。我们那一代人,对生存和工作有一种本能的珍贵,拿到一个工作不管你干啥,先把它干好,否则自己养活不了自己。
第五代导演在那时受到了国际影评人的注意。那时候参加国际电影节最大的受益是不停的看电影,这个电影节结束就买经济舱机票飞到下一个再去看,不停的看,不停的交流,不停的学习。大家是互相促进的,有时候你的开悟不是系统学了多少,而是某一句话激活了你多少年的积累。电影就是做交流产品,而我大概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。
现在
不够艺术家的位置,我是一个匠人
我是拍文艺片出来的,我发现文艺片的导演们容易批评商业片的导演,但商业片的导演很少批评文艺片的导演。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两个系统的东西,正因为这两个系统同时存在,电影才丰富多彩。
我后来一直想做中国的市场电影,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有了一点点成绩,这不是我个人的,而是大家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,共同努力。
最早其实没有人想要我这个监制。监制应该起到什么作用?第一任务是保护导演,你要建立一堵墙,现在电影越来越多的多方投资,有一些是专业投资公司,很多不是,如果每个人都去跟导演谈想法,那导演还要拍戏吗?所以监制要挡在前面。
第二是规划好从头到尾电影流程,使导演们永远在他的位置上。我们现在的导演有点压力太大,啥都得管。单纯性是艺术最宝贵心理动机,所以制片团队、监制都要完成你的第一任务,就是保护创作,而不是干涉。

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,我为什么还是喜欢做监制这件事?我一直认为我不够艺术家的位置,但我是一个很好的匠人,我很擅长学东西。
转到商业的方向,我们发现电影最容易让观众接受的形态是感性形态。做电影这个很重要,你的情节段落是不是能够从感性上激活观众心底(的情感)很重要,我们还是从世界电影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比如我们复盘过《长津湖》。我是编剧之一,我们有很多问题,它仓促、几个导演拍、风格衔接难度很大。但是《长津湖》解决了一个战争片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,就是“追随”。
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他的心要追随某个东西而行,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。《长津湖》写了第九兵团里面的一个连的死亡史。开头陈凯歌导演拍的部分就需要观众喜欢上这批人,观众喜欢,他们就会追随这六个人,直到最后牺牲只活下来一个。人物也是商业电影核心,要有更通俗的情感,把大众的共鸣写进我们的角色,放到大的背景里去跟随。

艺术电影有时候感性的点比较高,大部分人跟不上。你不能在电影院里将观众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作为前提去拍电影,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电影受众太窄了。
比如谢晋导演,曾有人说他的作品过时了。但这一两年,他在豆瓣里有好几部作品突破了9分。这是因为他的故事讲的好,故事里面讲了人类的理想,讲了人文的基本架构。这是历史长河对本质问题的评价,本质问题历史越长越看得清楚,相反时髦的东西都是短的,但时髦的东西也会改变一代人的风貌,这是我的经验。
未来
AI将带来翻天覆地变化,群体观影需求无可替代
我对科幻是有一些好奇的。比如这一次平遥说到关于AI的讨论,我的直觉告诉我,中国电影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挑战。就像在默片年代卓别林是至高无上的,所以有声电影发明以后他拒绝拍摄。但替代是必然的,AI出现带来的变化也是这样。
我最近看了关于人工智能的书。在我的理解里,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定义,我们知道电脑程序会发出指令,这个词告诉我们电脑是你的工具,但是在AI的面前,科学家说是对话,什么叫对话?智能之间的平等交融叫对话。我个人认为,AI不是工具而是交朋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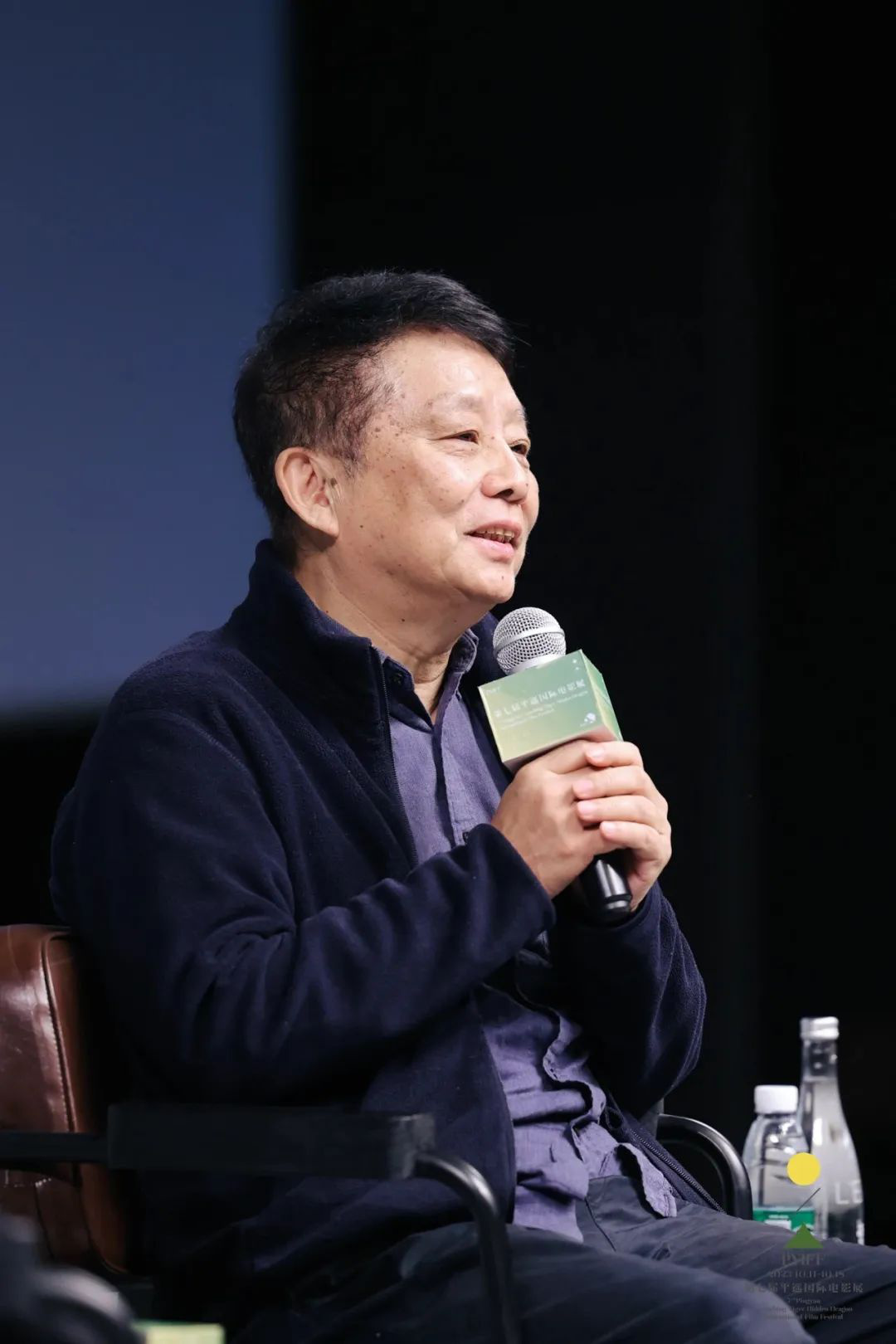
有科学家得出了所谓“筛子”理论:AI系统的阅读速度和智商是人类的一千倍到一万倍之间,假如它阅读了贾樟柯导演的风格还有其他导演一千部、一万部作品,或许它还无法出入自如,但在“过筛”后对内容进行重新储藏和梳理,它的知识系统将是一个多人的综合体。
AI还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?我看到了它在虚拟空间中的再造能力。未来,可能只需要几个具有想象力的人加上技术保障团队就可以和AI合作完成一部电影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AI会给电影带来翻天覆地质的变化。
电影为什么比较敏感,因为电影和技术发展特别密切,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永远都跟电影发生着关系。但观众(走进影院的)观影需求是很难被替代的。场域里的情绪传染就是电影的魅力,目前还没有东西可以取代。


 凡人微光|重...
凡人微光|重... 如愿
如愿 微视频|丰收新景
微视频|丰收新景 青春华章|追光
青春华章|追光 丰收24小时
丰收24小时 青春华章·亿缕...
青春华章·亿缕... 聚一起 就是家
聚一起 就是家 亿缕阳光丨被...
亿缕阳光丨被... 微视频丨同行...
微视频丨同行... 土耳其水拓画...
土耳其水拓画... 新华全媒+|来...
新华全媒+|来... “中国历代绘...
“中国历代绘... 乌鲁木齐“热...
乌鲁木齐“热... 松花江哈尔滨...
松花江哈尔滨... 我国成功发射...
我国成功发射... 产教融合促就业
产教融合促就业 北京市民快乐...
北京市民快乐...